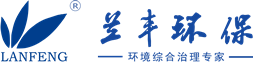“蛋糕”大小VS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
把企業(yè)這塊“蛋糕”做大,大概是每個(gè)企業(yè)家的愿望;能否將企業(yè)“蛋糕”做大,顯然不是“人有多大膽,地有多大產(chǎn)”,而是取決于其市場(chǎng)競(jìng)爭(zhēng)力。沒(méi)有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的企業(yè)也就無(wú)市場(chǎng)競(jìng)爭(zhēng)力可言。企業(yè)只有成功地尋求到、保持以及捍衛(wèi)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,才能成為市場(chǎng)的“主宰”。那么,企業(yè)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從何而來(lái)呢?
始自20世紀(jì)80年代的探索延續(xù)至今,并在西方戰(zhàn)略管理學(xué)界形成了三大學(xué)派。一是結(jié)構(gòu)學(xué)派,代表人物是邁克爾·波特。他從產(chǎn)業(yè)組織理論的“結(jié)構(gòu)-行為-績(jī)效”這一范式出發(fā),認(rèn)為企業(yè)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是由一個(gè)產(chǎn)業(yè)中新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對(duì)手的進(jìn)入、替代品的威脅、買方的討價(jià)還價(jià)能力、賣方的討價(jià)還價(jià)能力和行業(yè)內(nèi)競(jìng)爭(zhēng)對(duì)手之間的競(jìng)爭(zhēng)五種力量決定的。二是資源學(xué)派,代表人物是沃納爾特(B.Wernerfelt)、科利斯(David Collis)和蒙哥馬利(Cynthia A.Montgomery)等。他們的主要觀點(diǎn)是企業(yè)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來(lái)源于其擁有或支配的具有價(jià)值性、稀缺性、非模仿性、非流動(dòng)性的企業(yè)資源,特別是對(duì)企業(yè)非物質(zhì)性的無(wú)形資產(chǎn)的開(kāi)發(fā)利用。三是能力學(xué)派,代表人物是哈默爾(Gary Hamel)和普拉哈拉德(C.K.Pahalad)。其主要觀點(diǎn)是企業(yè)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來(lái)源于自身所具有的能力,正是企業(yè)能力的差異造成了企業(yè)效率和收益的差異。
按照結(jié)構(gòu)學(xué)派的邏輯,同一產(chǎn)業(yè)內(nèi)的企業(yè)經(jīng)營(yíng)狀況應(yīng)該是差不多的。但事實(shí)上,無(wú)論“夕陽(yáng)產(chǎn)業(yè)”還是“朝陽(yáng)產(chǎn)業(yè)”,企業(yè)經(jīng)營(yíng)狀況是“遠(yuǎn)近高低各不同”。資源學(xué)派的邏輯結(jié)論是,企業(yè)要贏得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太簡(jiǎn)單了—守著企業(yè)優(yōu)勢(shì)資源睡大覺(jué)就行了,但端著資源“金飯碗”沿街“乞討”的企業(yè)也并不鮮見(jiàn)。因此,結(jié)構(gòu)學(xué)派側(cè)重于對(duì)產(chǎn)業(yè)內(nèi)外相關(guān)企業(yè)的相互關(guān)系和力量對(duì)比的研究,忽視了企業(yè)內(nèi)部要素的作用與影響。資源學(xué)派強(qiáng)調(diào)了資源稟賦作用,但它不僅忽略了企業(yè)所處的外部環(huán)境,同時(shí)也見(jiàn)物不見(jiàn)人,漠視人的價(jià)值和人的主觀能動(dòng)性。只有能力學(xué)派,既關(guān)注到了企業(yè)的內(nèi)外部環(huán)境,同時(shí)又將物的要素和人的精神有機(jī)結(jié)合起來(lái),才是探求企業(yè)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的正途。簡(jiǎn)言之,結(jié)構(gòu)學(xué)派分析的是企業(yè)贏得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的環(huán)境,資源學(xué)派解構(gòu)的是企業(yè)贏得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的基礎(chǔ),而能力學(xué)派揭示的才是企業(yè)贏得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的源泉。
管理的核心任務(wù)
事實(shí)上,企業(yè)能力是企業(yè)邊界的一個(gè)決定性因素,企業(yè)能力的強(qiáng)弱、大小決定了企業(yè)邊界的具體位置。當(dāng)今世界,收購(gòu)、兼并、合并和聯(lián)合是把企業(yè)這塊“蛋糕”快速做大的捷徑之一。決定企業(yè)這種擴(kuò)張方式能否成功的關(guān)鍵正是企業(yè)能力。
1997年8月4日,波音正式完成與麥道的合并。這種高起點(diǎn)的聯(lián)合,形成了航空制造業(yè)新波音與歐洲空中客車公司兩雄稱霸的新局面,也使波音在世界500強(qiáng)的排名,從1996年的第144位一躍為1997年的第39位。
l998年7月3日,德國(guó)大眾汽車以4.3億馬克的價(jià)格收購(gòu)英國(guó)勞斯萊斯汽車公司,這不僅使德國(guó)大眾擁有由勞斯萊斯創(chuàng)造的獨(dú)特的、同行難以企及的在驅(qū)動(dòng)力、減噪、安全舒適性方面的汽車核心技術(shù),同時(shí)也為德國(guó)大眾進(jìn)入英國(guó)市場(chǎng)降低了門檻,由此實(shí)現(xiàn)了快速做大的目標(biāo)。
波音和大眾之所以能擴(kuò)張成功,緣于這種“合二為一”在其企業(yè)能力控制范圍之內(nèi),在其“勢(shì)力范圍”之內(nèi)。如果企業(yè)自身的能力無(wú)法達(dá)到這個(gè)境界,強(qiáng)行將“蛋糕”做大,其結(jié)果必然是可望而不可及,甚至事與愿違。國(guó)內(nèi)把組建企業(yè)集團(tuán)作為國(guó)有企業(yè)重組、行業(yè)重組的一種主要形式。當(dāng)時(shí),人們把“船大抗風(fēng)浪”當(dāng)成對(duì)企業(yè)集團(tuán)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的一個(gè)形象描述。一時(shí)間,全國(guó)上下組建企業(yè)集團(tuán)的活動(dòng)“風(fēng)起云涌”。不可否認(rèn),有一些企業(yè)通過(guò)兼并、聯(lián)合等多種形式組建的企業(yè)集團(tuán),實(shí)現(xiàn)了優(yōu)勢(shì)互補(bǔ),提升了競(jìng)爭(zhēng)力,發(fā)展勢(shì)頭良好;但同時(shí)也有一些企業(yè)在組建成企業(yè)集團(tuán)之后,企業(yè)形勢(shì)不僅沒(méi)有好轉(zhuǎn),反而資產(chǎn)質(zhì)量迅速下降,企業(yè)原有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喪失殆盡,企業(yè)集團(tuán)到了崩潰的邊緣。由此可見(jiàn),企業(yè)管理最深層次的任務(wù)或許就是要構(gòu)造企業(yè)的能力!
核心能力:文化力
企業(yè)本質(zhì)上是一個(gè)能力的集合體,包括生產(chǎn)能力、資金運(yùn)作能力、新產(chǎn)品開(kāi)發(fā)能力等。企業(yè)的核心能力就是在企業(yè)能力結(jié)構(gòu)中居于支配地位、發(fā)揮決定性作用的能力。
許多學(xué)者都認(rèn)為,所謂企業(yè)的核心能力是指一個(gè)企業(yè)獨(dú)有的、扎根于組織之中的、適應(yīng)市場(chǎng)機(jī)會(huì)的、能形成可持續(xù)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的能力。這種能力在本質(zhì)上是一個(gè)企業(yè)“特定的知識(shí)體系”。正如美國(guó)管理學(xué)家潘漢爾德和哈默所說(shuō),核心能力是“組織中的積累性學(xué)識(shí),特別是關(guān)于如何協(xié)調(diào)不同的生產(chǎn)技能和有機(jī)結(jié)合多種技術(shù)流派的學(xué)識(shí)”。無(wú)疑,這種企業(yè)“特定的知識(shí)體系”是以隱性知識(shí)為主的,并且具有明顯的方法論特征,是很難察覺(jué)、復(fù)制和模仿的。因此,在其概念理解上存在的種種歧義就用不著大驚小怪了。例如,有人認(rèn)為企業(yè)核心能力等于核心技術(shù)或先進(jìn)設(shè)備等等。索尼的微型化技術(shù)、佳能的精密儀器研制、NEC的數(shù)字技術(shù)、松下的加工技術(shù)和分銷能力、耐克的銷售能力和設(shè)計(jì)能力、戴爾的直銷能力、海爾的市場(chǎng)整合能力、長(zhǎng)虹的技術(shù)吸收創(chuàng)新和低成本擴(kuò)張能力等等,被研究者或企業(yè)家個(gè)人描述為相應(yīng)公司的核心能力。
這些林林總總的表述并沒(méi)有把握問(wèn)題的本質(zhì)。由于企業(yè)核心能力是“特定的知識(shí)”,因此其最終必須歸結(jié)到人的方面并以人為載體,是隱藏在企業(yè)資源背后的配置、開(kāi)發(fā)、保護(hù)、使用和整合資源的主體能力。任何僅僅將企業(yè)某一項(xiàng)專有技術(shù)、壟斷資源或暢銷產(chǎn)品視為企業(yè)核心競(jìng)爭(zhēng)力的企業(yè)都不會(huì)成為百年老店,因?yàn)樗鼈兪菍?duì)物的依賴而不是對(duì)人的依靠。而企業(yè)的真正核心能力應(yīng)該是以人為皈依的“企業(yè)文化力”。
只有文化的力量才是最深刻、最終極的力量。以滿人入關(guān)為例,他們攻破了漢人的長(zhǎng)城,奪取了漢人的城池,推翻了漢人的江山,在政治上、軍事上是勝利者。但在文化上,他們卻失敗了—滿人入關(guān)后,被漢人同化了;雖然是滿人坐了江山,最后也相當(dāng)于漢人坐了江山,不過(guò)是換了個(gè)朝代。文化是滲透到血液里的東西,它決定了大腦怎么思維,決定了雙腿怎么行動(dòng),因而是最終的力量。
企業(yè)文化對(duì)企業(yè)能力的形成、作用、保持和促進(jìn)起著根本性的作用,決定著企業(yè)在市場(chǎng)活動(dòng)中的態(tài)度,企業(yè)產(chǎn)品、服務(wù)屬性的價(jià)值取向,企業(yè)自身的組織規(guī)范和行為準(zhǔn)則,企業(yè)用什么樣的方式、手段來(lái)運(yùn)用企業(yè)的資源參與市場(chǎng)競(jìng)爭(zhēng)。這些都是企業(yè)能力形成的前提條件和后續(xù)保證。所以,企業(yè)文化力是企業(yè)的核心能力。
“五力模型”
企業(yè)擁有的文化力才是企業(yè)長(zhǎng)期競(jìng)爭(zhēng)優(yōu)勢(shì)的真正源泉,構(gòu)造、積累、保持、運(yùn)用文化力是企業(yè)生存和發(fā)展的根本性戰(zhàn)略,也是企業(yè)經(jīng)營(yíng)管理的永恒目標(biāo)。計(jì)劃、組織、協(xié)調(diào)、控制等各類管理職能都是圍繞企業(yè)文化力而展開(kāi),生產(chǎn)、營(yíng)銷、財(cái)務(wù)等各個(gè)管理領(lǐng)域都應(yīng)該是以企業(yè)文化力為中心。
那么,企業(yè)文化力是一種什么樣的“力學(xué)結(jié)構(gòu)”呢?在管理學(xué)的視域下,可以將“企業(yè)文化力”解構(gòu)為五種力量形態(tài)。
卓越的領(lǐng)導(dǎo)力 根據(jù)美國(guó)著名學(xué)者詹姆斯·庫(kù)澤斯和巴里·波斯納的觀點(diǎn),領(lǐng)導(dǎo)力是領(lǐng)導(dǎo)者如何激勵(lì)他人自愿地在組織中做出卓越成就的能力。它表現(xiàn)為企業(yè)領(lǐng)導(dǎo)團(tuán)隊(duì)具有的超凡的戰(zhàn)略思維、戰(zhàn)略決策能力以及組織協(xié)調(diào)能力等等。
高效的執(zhí)行力 高效的執(zhí)行力是以高度自覺(jué)、行動(dòng)一致的員工隊(duì)伍為根據(jù)的,同時(shí)又以完善的企業(yè)考核、激勵(lì)制度為條件的。
持續(xù)的學(xué)習(xí)力 企業(yè)間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實(shí)際上是學(xué)習(xí)能力的競(jìng)爭(zhēng)。學(xué)習(xí)力在本質(zhì)上是企業(yè)的適應(yīng)能力、模仿能力、接受能力和創(chuàng)新能力的總和。由于企業(yè)所處的環(huán)境永遠(yuǎn)是變化的,這就決定了學(xué)習(xí)力必須是持續(xù)的。
強(qiáng)大的凝聚力 它是企業(yè)團(tuán)隊(duì)意識(shí)和團(tuán)隊(duì)精神的體現(xiàn),是企業(yè)具有的團(tuán)結(jié)、凝聚員工的能力。顯然,只有當(dāng)全體員工把自己的利益同企業(yè)的經(jīng)營(yíng)好壞緊密聯(lián)系在一起,與企業(yè)同呼吸共命運(yùn),同舟共濟(jì),才能極大地?zé)òl(fā)其工作熱情,激發(fā)全體員工的能動(dòng)性和創(chuàng)新精神。
優(yōu)美的形象力 它有利于企業(yè)在激烈的市場(chǎng)競(jìng)爭(zhēng)中獲得政府的支持、客戶的信賴、銀行的貸款和社會(huì)的好感。優(yōu)美的企業(yè)形象不但是企業(yè)的無(wú)形資產(chǎn)和潛在財(cái)富,同時(shí)也是企業(yè)走向市場(chǎng)、參與競(jìng)爭(zhēng)的重要力量。
- 當(dāng)前位置:首頁(yè) > 新聞資訊 > 一展風(fēng)采
- 一展風(fēng)采
- 上一篇:企業(yè)家談管理
- 下一篇:鹽城民俗俗得可愛(ài)
 |
|